《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册)与我们熟知的文学史有很大不同,中国文学史的常规印象是严肃、条理清晰,但王德伟带给我们的文学史却像散布在浩瀚夜空中的繁星,又像深海中美丽的珍珠。
他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不一样的文学之窗。窗外的风景看似自然随意,但栽种的每一株植物都是精心栽种的,哪怕是一丛灌木、一条小溪,都有他精妙的安排和用心。他希望这些散落、放射状的呈现,能以小见大,并透过不同时点所形成的脉络与空隙,留给大家想象的空间,从而呈现出一个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文学世界。徜徉其中,透过每一枝一叶、一花一蕊,都激起我们对草木世界的沉浸、新奇甚至向往,进行一场生命与自然、生命与生命的对话,那将是多么有趣而美好的境界啊!
用非常文学的方式写文学史,几乎是一种奢侈。多年以来,文学史的叙事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标准,但王德伟却联合143位作家,用161篇文章,写出了这部独一无二的文学史长卷。这些文章有的夹杂着议论、叙述,有的则是亲身经历,有的则是虚构的场景……他从一开始就打出了讲好文学故事的旗号,邀请了众多作家加入到文学史的写作中来。王安忆写到了母亲茹志娟;余华写到了自己在华东师范大学翻墙的故事;莫言写到了今天阅读和写小说的意义……王德伟希望这本讲述中国文学在世界的著作,展现出“文学”的广度,并试图大胆地进行文学实验。星光熠熠、云雾缭绕的文学现象在王德伟神奇的指挥棒下,闪烁着特殊的风采和智慧,文学的格局和历史的时空被无限拓展。
采访时间定在8月7日。王德伟不用微信,我们通过电话和邮件交流。按下那12位数字,我便进入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构建的文学海洋。
读书报:《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版筹划已经很久了,对吗?
王德伟:是的。因为留学期间在海外接触广泛,所以有不同的体会。很多在文学院受启蒙的同事,可能对文学史教育有些困惑:时代、大师、运动……差不多都一样,这些当然很重要。其实个人的生活、环境、历史,有很多层次、很多方面。文学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事业。想象不是天马行空的幻想,而是与现实的结合,基于生活本身的经验,进行创造甚至预想,并给出陈述——任何学科都有陈述。浓缩在文学领域,直白地说,文学是一门叙事学科。各种学术、创作方面,是文学很特殊的方面,文学史的编撰需要大胆地呈现。
哈佛大学出版社策划了一套名为“新文学史”的丛书,鼓励我尝试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我在写《哈佛新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就想到了非华语世界的读者。如果我们说鲁迅伟大,他们可能只知道事实,却不知道原因。作为编辑,说服力很重要。我不是直接卖“伟大、伟大、真伟大”,而是把鲁迅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呈现出来,让他们知道鲁迅的伟大,让他们好奇,希望读到更多鲁迅的作品。
在哈佛《新文学史》丛书里,无论人物是大是小,他们都站在时间的节点上,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历史和时间的流动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们选择和讨论的话题,希望能够散发出文学史的复杂面貌。不管读者是什么样的,至少让他们知道文学是什么样子。文学就是讲故事。我联系了100多位作者,我说:我们先把事情讲清楚,最好读者能读完这2500字,对这本书产生兴趣。这是我进入文学史的方式。《新文学史》可能不会成为教科书,但我希望它对推动文学的发展有所帮助。
读书报:为什么采用“年代模式”?以年份为纲,会不会有些作家被分在不同年代记载?这种形式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王德伟:“编年体”和“事件纪年”其实来自中国古典历史叙事的规律。在这本书中,我有意识地使用——或者至少是暗示——它作为整个文学史话语的根本形式。一方面,我指出看似争议性的历史事件,最终都会回归到历史流动的底线。另一方面,我也有意向传统致敬,并将其与当代解构主义者的历史观区分开来。中国传统与现代文明中对“文学”与“历史”的重视,值得我们不断检讨和反思。
一般文学史强调宏大叙事,以大师、经典、事件作为话语的起点、发展、过渡和终结部分。《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尊重宏大叙事的历史视角和权威性,但也关注“文学”在遭遇历史时所展现或隐藏、想象或记录的独特能量。如何有意识地凸显文学史的“文学性”本质,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历史书写,是我面临的首要挑战。因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未必能被学科建设所接受。习惯了正统文学史的读者难免会感到失落。
哈佛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面向大学以上学历的普罗大众,风格简洁易读。中文版读者或许对很多历史和文学事件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会抱有更大的期待。本书的多焦点叙事或许难以理解。但我希望这本书能引起读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多元面向的兴趣或争论,重新思考“文学”的形式和潜力。
读书报:您曾说:“没有晚清,就没有五四运动。”这次您把“现代性”延伸到了明末。书中的“现代性”其实延伸了近200年——您如何理解“现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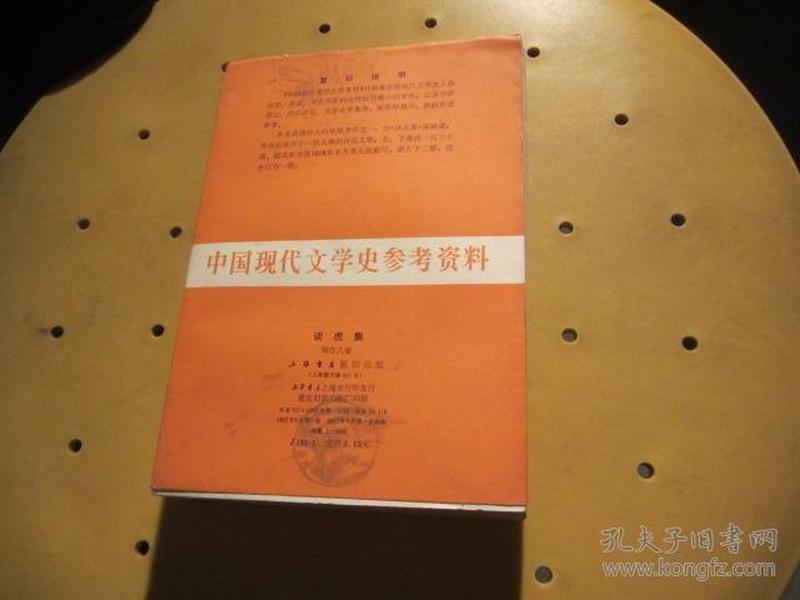
王德伟:其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计文夫、周作人从左右不同的立场,都把中国现代性追溯到了晚明(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以此为开端);日本京都学派甚至把宋代作为中国现代性的起点。这种回溯可以无限延伸,但恰恰是我希望打破的迷思:我们不再问“晚清”或“五四”是现代性的开端,而应该问“为什么”某个时点或某种话语把晚清或“五四”看作现代性的开端。比如,以古鉴今、言简意赅为纲、主张制度变革的儒家经学“公羊学”,沉寂了一千年,为什么在晚清突然兴起,成为维新派的借口? 换句话说,我们的问题不再是一个起源问题,而是一个考古学问题。
《被压抑的现代性》发表至今已二十多年,很多可能并不完整的论证被后人强化,而一度被视为劣等的晚清现象,却反而引领了当代潮流。进入21世纪以来,科幻小说蓬勃发展,甚至受到全球关注。回顾晚清最后10年的科幻热潮,仿佛历史在重演。当然,历史不会重演,将过去与现在或任何时间点进行联系和对比,并定义意义,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历史的行为。
延续“没有晚清,哪有五四”的命题,我们甚至可以推论出另一层辩证法:“没有五四,哪有晚清”。五四的意义坐标是如此多元,让我们看到许多新旧知识分子的斗争与疑问,从而理解他们道路的曲折。正是因为五四带来的启蒙思想,我们才得以充分发挥主体的“先入为主”地位,重新看到被帝国话语和被压制又回归的冲动所埋藏的无数改革机遇。五四可以看作是一个祛魅的时代,更是一个召唤精神的时代。
读书报:您如何看待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下限设定为“当代作家韩松幻想的2066年”?科幻虚拟的时间能构成历史吗?
王德伟:这本书的时间点始于1635年,终于2066年,确实为这段文学史的叙述提供了一个想象性和辩证性的层面,从而重新问题化了什么是“文学”、“文学”史、“文学史”这些古老的话题。
文学史的时间充满着共时性的“厚度”,1935年便是一例。这一年,漫画家张乐平(1910-1992)的漫画《三毛流浪记》大受欢迎;前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在福建被捕,临死前留下《多余的话》;影星阮玲玉(1910-1935)自杀身亡成为媒体焦点;河北定县农民首次上演《过渡》《龙王曲》等实验话剧。文学史的时间里,蕴含着考古学的后见之明。
1971年,美国加州《天使岛诗集》首次向公众出版,再现了19世纪来美中国工人的悲惨遭遇;1997年,耶鲁大学孙康义教授终于解开了50年前父母为何受困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谜团。文学史的时光,也能揭示命运的神秘轮回。
1927年,王国维(1877-1927)跳湖自杀,陈寅恪(1890-1969)撰写墓志铭:“独立精神,自由思想。”42年后,陈寅恪悲痛地去世,他为王国维撰写的墓志铭也成为他自己的挽歌。
最后,文学史的时间被投射到未来。科幻作家韩松认为,2066年,人工智能将席卷宇宙,随后火星人占领地球,人类文明将灭亡,如同沧海一粟。这是未来的“文学”史。或许,只有站在文学的角度,我们才能想象历史的可能与不可能。
读书报:您觉得这部书的编撰方法上有哪些创新之处?
王德伟:一些有识之士可能会觉得这很眼花缭乱,只是一场闹剧。但我想强调一下闹剧背后的秘密。这里涉及的问题,不仅是文学史的内容,更是“文学”与“历史”的辩证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学科体系内对“文学”的狭隘定义。讨论学术对象,一定要谈小说、新诗、戏剧、散文;讨论作家,只谈鲁、郭、毛、巴、曹;讨论现象,只谈各种现实主义加上革命启蒙和寻根先锋。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太熟悉而无法自拔的叙事声音,劣等者甚至露出了八股文的腔调。 但进入21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如果依然秉持上世纪初以来的规范,忽视与时俱进的媒介、领域、流派的变化,则会自成体系。
读书报:对于文学、美学、电影、戏剧、网络诗歌等,有没有统一的标准或者原则来选择哪些文章可以进入文学史?
王德伟:本书对“文学”的定义,不再是标准术语,而是试图呼吁对“文”进行一个宽泛的定义——痕迹、符号、审美产物、气质、自然与思想的文化。“文”不仅指天文、地理、人文,在现代语境中,文学的物质性、媒介性也是我所关注的。

我们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形成于20世纪初,堪称现代的发明。21世纪,我们面临的人文环境与过去不同。在尊重学科体系的教育功能与传承性的前提下,我们不妨重新思考“文学”与“学术”和“历史”之间的关联。这是对传统的致敬,也是创新的努力。
本书收录的多元文本与现象或许也引人关注。每篇文章对体裁、主题、媒介的处理更是多种多样,从晚清画报到当代网游,从革命启蒙到鸳鸯蝴蝶,从伟人演讲到狱中书信,从红色经典到离散叙事。不仅如此,作者的文风也各有特色。按照编辑格式,每篇文章都从特定的时间、文本、对象、事件出发,然后“各奔东西”。有的文章夹杂着讨论与叙述,有的是个人故事,有的甚至是虚构的故事。这与我们熟悉的标准文学史叙事大不相同。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文章仍然围绕基于文本的文学,思考20世纪文学所经历的各种命名与更名过程,以及“内因”与“外因”的互动,有些被认可,形成主流话语,有些则被忽略、被压制,成为文学挖掘的堆积或断层线。
读书报: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史?阅读《新编》的过程是对文学史认识的一次颠覆,总会有一些新鲜的感受,同时也会有批评的反思。《新编》中您最看重的是什么?
王德伟:无论持何种立场,一般的文学史都是以历史的风格来书写的。新版《文学史》无意冒犯这一模式的重要性——它的存在正是这本新版《文学史》的基石。但我认为,除此之外,还值得思考的是“文学”史不同于其他学科史的特点。我们应该再次强调文学史内涵的“文学性”:文学史的写作应该像它所关注的文学作品一样具有文本意识。但我所说的“文学性”并不一定要局限于审美形式;对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的判断或欣赏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必须不断加以强调和审视。相应地,新版《文学史》的作者们以不同的风格处理文本内外的现象,力求实践“文学性”,这是一种自觉的“写”历史的态度。
读书报:您跟作家是怎样沟通的?
王德伟:我的工作极其繁忙,我又是一个内敛保守的人,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的信息交流,朋友和学生发给我的信息我都用不上。网络时代,通讯当然很发达,Facebook、微信、QQ……我一个都不用。电子邮件已经很丰富了,不加入社交媒体生活更简单,就只是隐居。学生和朋友觉得我无知,一定不知道这个不知道那个,他们会通过邮件或电话告诉我重要的信息。第二天我就知道了“二叔”事件——但我还是庆幸自己不在微信的世界里。
读书报:您研究文学几十年,读了那么多书,写了那么多作品,您觉得作家的生命力有哪些特点?
王德伟:这个很有意思,有的作家一夜成名,但都是昙花一现,有的甚至幸运地再也没有继续写下去。对有的作家,我看到他们中后期的作品,就替他们担心,想着他们最好在某一年或某一月的巅峰停下;有的作家依然一如既往地优秀,创意无穷,比如王安忆。我很佩服她的创造力,可能不是每一本书都是100分,但基本都是优质作品,她从不给自己设限。创作很费时费力,创作风险很大,是一门“表演艺术”,像换了个样子,在文字的舞台上表演。作为文学史研究者,我是一个敬业的读者,只是静静地读他们的作品。我钦佩一些经过多年磨练,成为职业作家的作家,他们经验、方法、技巧都炉火纯青,就像一个精益求精的工匠。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是如此。
读书报:您提到新编出版关心的是如何赋予中国传统文学与历史的对话以当代意义,您觉得达到了您的初衷吗?
王德伟:我多次强调,这部文学史有一个实验性的前提,无论在方法的建构上,还是在编撰的过程中,都有不完整的一面,但“不完整”和“在世”也是这本书的概念之一。
读书报:作为海外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著名学者,您如何看待《新编中国文学全集》在世界讲述中国文学故事的意义和价值?
王德威:作为在海外教授、研究中国人文的学者,我们必须体会到这个传统本身的复杂性与活力,或者我称之为“内心世界”的能量。我们不必局限于国家的地理局限,而可以呈现现代中国更广阔的历史与文学视野。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