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
南京大学文学院余斌教授多年来一直为学生讲授“外国文学史”和“西方文学名著精读”等课程,影响了南京大学众多学子。余斌教授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阅读和写作经验,推出了《译林世界名著讲座》一书。书中选取了《伊利亚特》《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傲慢与偏见》《了不起的盖茨比》《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外国文学经典,以幽默活泼的方式进行解读,并附上名人评论、中译本出版简史和原创插图。本文获授权摘录余斌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后记,书名由编者撰写。

《译林世界经典讲义》内页
为什么要读经典?这是一个问题;如何读经典又是另一个问题。无数人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答案,事实上也有很多经典的例子。比如,当代西方文学的两位大师卡尔维诺和纳博科夫都有一篇著名的文章,题为《为什么要读经典?》,后来被用作一本书的书名;纳博科夫则有一篇《文学讲义》,讲解了几部西方文学的名著,尤其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然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些都是精辟之作,太过高深,或者难以效仿——有多少人能像纳博科夫一样,花那么多时间去体味细节,品味骨子里的韵味?
“为何读经典”的问题,其实和“为何读书”是一样的。这里所谓的“书”已经预设为“好书”,而“读书有益”显然不包括坏书。按照“读书有益”的标准,很多看起来像书的东西,其实都不能算作书,只能称为阅读材料。
劝人读书的方法多种多样,诸如“黄金屋”、“美丽妻子”之类的诱惑是不能接受的,可以忽略。真正的要点应该与知识挂钩——书籍是知识的载体。连小学生都能背诵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很少有人提到苏格拉底的名言“知识就是美德”。“力量”是向外的,导致征服外界;“美德”是向内的,导致心胸的开阔和境界的提升。“力量”是有用的,但“美德”是否有用就很难说了。
我从1990年开始在大学任教,一直教外国文学。几乎每堂课的第一节课,我都会告诉我的学生,只要能通过考试,可以逃课,但我希望他们能认真读几本经典著作。我说的话没有任何虚伪之处——读书比循规蹈矩地上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这确实是我的亲身经历。直接面对经典,不经过“中介”。很多学生逃课都是有充分理由的,这也在我的预料之中,我也不着急。但时间越长,我越怀疑他们是否利用了这段时间去读书。能做到我想做的事,必须有一个前提:每个人都相信那些书值得读,或者有趣,或者有益。而这并非不言而喻的。
从来没有学生当面问过我,读经典、名著有什么用?一来这样的问题太过唐突,等于是在挑战“读书有益”这句古话;二来我猜学生会认为得到的答案无非是“无用之用才是最大用”,是一些老生常谈的“大道理”。大道理之所以是“大”道理,是因为它必须、应该被带出来,但它终究是不及物的。而任何没有经过亲身体验验证的真理,都逃脱不了成为“大道理”的命运。
虽然没人问过这个问题,但我知道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其实,不仅仅是外国文学,在如今“实用主义”的氛围下,人文内容已经变得华而不实、肤浅,它到底有什么“用”呢?至于文学名著,“进”不能帮助求职、升学,“退”不能像网络文学、电子游戏、影视节目那样让人放松享受,读了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我们不能说绝对,至少中小学语文课外必读,大部分都是中外名著,都列入教学大纲,考试中也会涉及。怎么能说读名著没用呢?垫脚石才是所谓“有用”的正确答案。然而,这里的有用恰恰是把阅读的本义给抹杀了。
读书的本义是读书本身,其他一切都是加在读书过程中所获得的快感和满足感上。如果读书过程枯燥无味,那一切都毫无意义。要使阅读经典成为一种享受,前提是放弃有用或无用的考量。就说经典无用吧。它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无用——如果“有用”的“用”是指实用性的话。“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论”盛行。作为反击,还有一句话成为“共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不怕”。这是“手有千金不如身有本事”在特殊情况下的变体,强调的是“本事”。经典与“本事”无关。现在,或许是时候“正视”这一点了:如果无用,那读什么书? 我们不妨从另一个意义上弘扬“读书无用论”,就像“事先说坏话”一样,抛开实用主义的干扰,开启一场真正的经典与名著之旅。
…………
糟糕的是,在我们还没有用正确的方式打开经典之前,我们的偏见就已经形成了:经典意味着枯燥乏味,如果非要读经典,就必须端正心态,做好充分的准备,强迫自己去读——仿佛读经典就等于剥夺人们读书的乐趣。中小学必读书目成为了一种反向提醒,强行摆在人们面前的书籍总是令人厌恶的,于是尴尬的局面就出现了,你越强调读经典的重要性,人们就越躲得远。在学校里,在接受了这个事实之后(也因为应试学习的效率),老师们开始不遗余力地帮助学生读书。重点是给每部作品总结出很多“知识点”,极端一点是要求学生通读甚至背诵,读经典本身就变得可有可无了。这样一来,经典在“知识点”的压制下就死了,一点乐趣都没有了。 对读经的恐惧似乎已经被经验所证实,因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打破这个循环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抛开对经典的刻板印象,直接走进比如《包法利夫人》的世界。如果我们对经典不“傲慢”,我们确实有很多“偏见”。尊重经典是对的,但认为经典高高在上,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你真的翻开书,就会发现很多文学经典乍一看只是庄严而已,这里的“尊严”往往是我们的偏见造成的。其实,相当多的文学经典在它们自己的时代,是和今天的畅销书一样受欢迎的。《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的欣赏,在当时的雅典几乎是全民的,更何况狄更斯和马克·吐温都是很受欢迎的小说家,《傲慢与偏见》至今仍很受欢迎。无数中国读者的经历,也可以证明西方文学经典已经成为他们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很多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读者,对《红与黑》、《安娜卡列宁娜》、《简爱》等书籍津津乐道、熟记于心,今天也有很多年轻读者,从中得到阅读的乐趣。
…………
留有“端正坐姿”的余地是因为读经典可以很有趣,但并不代表阅读过程从头到尾都是那么轻松。经典有它严肃的一面,不仅因为它直面社会、历史、人生,拒绝提供心灵鸡汤,更因为经典面对读者时,有它自己的矜持和尊严。它不同于通俗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迎合你的口味,有完全不同的阅读路径设定:你走向它;而不是它反过来走向你,甚至体贴地取悦你。所以躺在那里接受按摩式的被动阅读是不够的。你必须调动自己进入状态、进入情境,建立自己与书中世界的关联。
显然,只有建立关联性,阅读才不再是一种不得不做的外在行为。梁启超所谓的“熏陶、浸润、激发、启迪”,鲁迅所谓的“增长人的情怀”,都是基于阅读时的共情。博物馆里的古董,已经是欣赏的对象(虽然对古董产生共情也不是不可能),但文学经典不是。它们在一代代人的阅读下依然鲜活,而且通过阅读这个媒介,可以实现与当下世界的对话,因此更容易产生共情。
至于共情,当我们熟悉书中内容,主角与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时,更容易发生。但外国文学名著讲述的是来自不同文化的外国故事,讲述的是过去的故事。时空的隔阂仿佛被盖上了一层厚厚的壳,似乎很难找到对应的体验,因此很难有代入感。但人是可以调动自己的,所谓“思过千秋,看透万里”,才是极致的调动。穿过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不同风俗习惯等隔阂,就像打破外壳,进入内部。你会发现书中看似陌生的世界、陌生的人,其实有几分熟悉,甚至会发现与身边的世界和人有很多重合之处。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历经了时间的考验,超越了时空的界限,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读者,都能经常翻阅,觉得耳目一新。 在你的参与下,他们的过去完成时可以变成现在时并最终完成。
因为“太阳底下无新事”,社会在变,时代在变,甚至大自然也在“剧变”,唯独人性不会变。人性中高尚的一面——正直、善良、勇敢和人性中阴暗的一面——贪婪、嫉妒、吝啬,一直都在,是人性大戏不变的内容,古今中外皆如此。剥去外在的差异,还原到底,不同时空的人们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处境。文学经典提供了“原型”,人物原型,故事原型。我们不能说其他书籍是经典的“抄袭”,但可以说它们“变而不离精”。经典就是那个“精”,这个“精”是建立在人类的共性之上的。
…………
“名作”是个灵活的概念,和“经典”一样,全看字面层次和意义。除了《伊利亚特》、《俄狄浦斯王》、《神曲》、《浮士德》等少数作品外,入选作品均为小说,19世纪以后,全部为小说,没有别的原因。相对而言,叙事文学更容易谈,小说显然是文学家族中最受欢迎的体裁。
我不知道这样的选读和导读是否真如我所愿,能多多少少引起读者的兴趣,让他们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阅读外国文学,而不必纠结于哪些有用,哪些没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导读写得多么好,都不能代替阅读经典。
卡尔维诺曾说过:“学校和大学都应该强调,所说的内容永远不会比所讨论的书好;但他们却竭尽全力让学生相信,事实恰恰相反。价值观普遍被颠倒,即用引言、批评工具和参考书目作为烟幕,掩盖文本必须和只能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说出的内容——而中介总是声称自己比文本本身知道得更多。”
不幸的是,老师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他百分百相信这个说法,并做了这个工作,这是自相矛盾的。幸好他有自知之明。我只希望我的解释不构成“掩盖”或“掩盖”的程度较低。而摆脱“烟幕”的最好方法仍然是你自己去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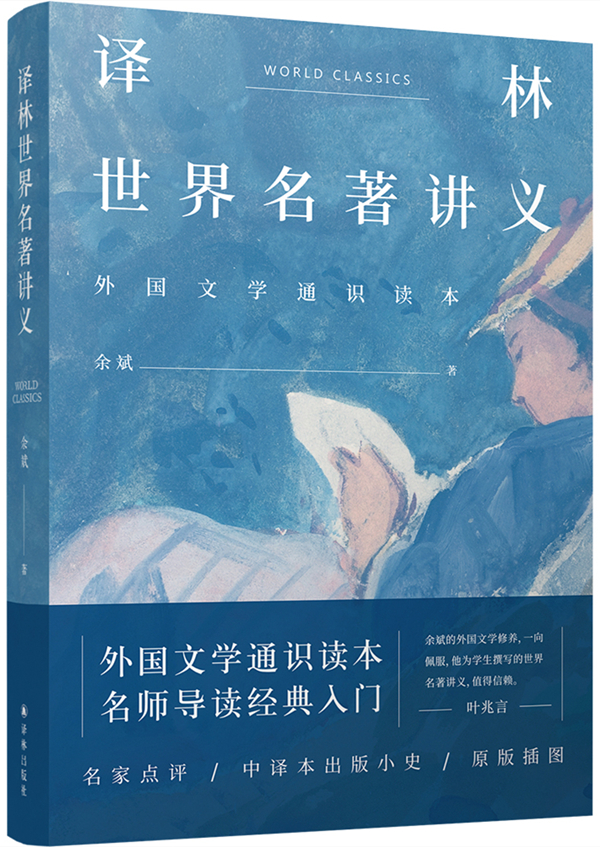
《译林世界经典讲义》,作者:余斌,译林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评论(0)